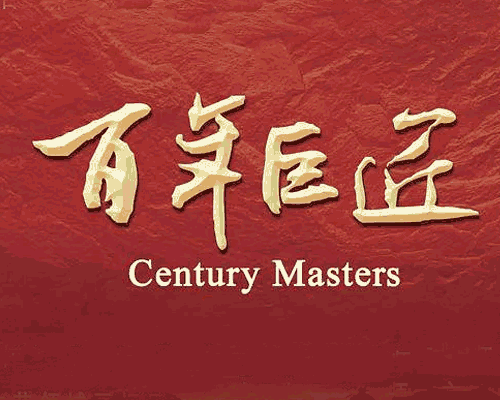创 建
请选择团队类型
1、DISC企业版(52题)
2、MBTI企业版(93题)
3、九型人格企业版(126题)
4、PDP企业版(30题)


| 1号 |
|
(0) |
| 2号 |
|
(0) |
| 3号 |
|
(2) |
| 4号 |
|
(26) |
| 5号 |
|
(0) |
| 6号 |
|
(27) |
| 7号 |
|
(0) |
| 8号 |
|
(58) |
| 9号 |
|
(0) |
| ENTJ |
|
(4) |
| ESTP |
|
(4) |
| ISTP |
|
(3) |
| INFP |
|
(2) |
| ISFP |
|
(1) |
| ISTJ |
|
(0) |
| ISFJ |
|
(0) |
| INFJ |
|
(0) |
| INTJ |
|
(0) |
| INTP |
|
(0) |
| ESTJ |
|
(0) |
| ESFJ |
|
(0) |
| ENFJ |
|
(0) |
| ESFP |
|
(0) |
| ENFP |
|
(0) |
| ENTP |
|
(0) |
| 高D |
|
(1) |
| DI |
|
(6) |
| DC |
|
(1) |
| 高I |
|
(0) |
| ID |
|
(0) |
| IS |
|
(0) |
| 高S |
|
(0) |
| SI |
|
(0) |
| SC |
|
(1) |
| 高C |
|
(1) |
| CD |
|
(1) |
| CS |
|
(2) |